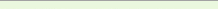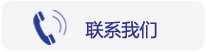君子風骨,自強不息
發布時間:2015年04月24日 點擊率:

——隨想龍南客家圍村
清晨任由導游領了,廿人一車徑直南行,由平原翻上高地,穿行于漫漫山隧,頗有些“曲徑通幽”之感。地陪正是贛南客家女,小麥膚色,明眸皓齒,嗓音清亮,歌調明麗,讓人暗暗叫好。聯想“一方山水一方人”,不由得念那圍村究竟地理何至、風土哪般,暗自揣測那是怎樣一番模樣了。
折出高速,兜轉于龍南山道,已是午后。復見村莊阡陌,正賞著春播勞作,不意那圍村已是近在眼前了。
客家——“土著”
導游稱“客家”,是為外來人。史有證,南宋戰亂,北方百姓避禍贛廣閩窮山之地,族居作圍,風俗作行,異于本土,故云“客家”。行于圍村,觀老者青衣抹額,嬰孩布兜于背,青團米果紅瓜子,珍珠湯香擂茶甜,其異趣可見一斑。最奇之處,自是這圍樓了。碉樓護圍、梅花墻眼、防火閘門、糯米糊墻、排水暗池、天井采光等等獨個來看,俱是異處。更遑論這關西圍、燕翼圍、烏石圍、八卦圍,各自所呈現之“國”字、環狀、半圓、八卦等獨特的建筑布局了。感嘆于客家文化之奇異,不由想那環繞圍屋的普通民居是否是當地人所建。導游似是能感應,直言現如今,此地的居民已分不出何人客家,誰是“土著”,龍南一帶俱認客家人,整個贛南方言通作客家言了。這才明了,無怪乎龍南人以傳承客家文化為己任了。
黃發——智慧
關西老圍中,偶賞古稀人含飴弄孫。如今之圍村,多只華發老者居于其間,間或伴有稚子圍膝。行在圍村,總能見到老者或三兩聚坐輕談,或獨自負手立門。我輩游閑之人,遇著異趣物事,躬問村中老嫗,老人頗為正視,細細綿綿解說一通,怎奈不懂客家言語,久久不明物事為何,白白費了老人心神,心下很是羞愧。老人觀我顏色,想是心下透亮,笑意慈和,并不為怪。別過老者,一時竟不能忘卻其容神——青布額箍,鶴發雞皮,行步蹣跚,眸色淺淡,但卻自有一番神韻引人生敬。轉頭踏入烏石圍,屋內老嫗分外淡定,任一行人觀己針黹,針腳不亂。男主人已近耄耋,不弓不蹣,導了眾人走祠堂穿天井,細說從頭。興許他的先輩也是如此傳其祖訓,教其“克紹先猷”吧。忽地憶起“燕翼”二字,取意《山海經》中“妥先榮昌,燕翼貽謀”,是深謀遠慮、榮昌子孫之意。關西圍、烏石圍也皆有或商或官的傳家之道。想來現在置身之龍南圍,物人事皆浸透歷史,滿是經歷。我想,圍子中的老人當是看盡世間事,滄桑代韶華,黃發皺紋淡眼里該俱是大智慧,故而使人肅然起敬吧。
清寂——生機
在關西圍中行走,突生別樣感受,起先也不明所以,直到貪看燕翼落后于大部分游伴,才明確這異樣緣何——龍南圍村頗靜。與三兩游伴步上碉樓,木梯傳遞震動輕緩,于廊上攝中院之月門,本還在祈求莫要有人往壞了景,結果長時間無人穿門而過,不由得笑了。這里不似西湖、烏鎮人潮熙攘,于圍中游賞之人,可謂零落。接踵、喧鬧并非圍村主調。偶爾游人穿行,至多為這份寧靜加入些許間奏。趕上游伴,剛入烏石圍之厚實圍門,踏入青磚鋪就,微濕微暗的院子,復又笑了——門旁白墻上,孩童以磚渣涂畫,線條簡單,好像是小鬼的樣子,頗有童趣,立時覺得圍村生機盎然。轉念想,龍南圍雖隱于深山,但確是阡陌交織、山道如梭,一代代客家人或耕耘于此或輾轉外出,客家人由此自強不息,傳承不止。于碉樓中眺望,群山環抱,想將圍村比作空谷幽蘭,又恐少喻了客家人的堅韌和智慧。圍屋旁有了新屋,新屋都不設碉樓、梅花眼,防盜御匪已是歷史事、過去時了。新屋上書寫“不能窮教育”、“建設新農村”標語,時代氣息濃烈。憶及電影《贛南村官》,會想那年輕的女客家大學生破除舊習,用知識造福一方的事,是否就發生在這里呢?即便不是,田里早已綠作一片的春苗,應當也喻示著希望吧。隔日,車輪千轉,關西、燕翼、烏石漸沒視野。別于來時昏昏,歸途還見圍村星散,或青顏雅致,或黃墻渾厚,或斷墻蔓草,令人顧盼。無怪乎傳“逢山必有客,無客不住山”,一眾圍村盡皆靜默,喧囂孤靜自得安寧。想來古之圣人所謂君子,不外如是了。客圍如斯氣質,若稱“風光”,意恐輕慢,視為“風骨”,倒覺貼近了些。
初游龍南畢。可嘆游不盡,龍南客圍三百座;自怨識不足,一樓一眼一磚事。隨行,隨想而已。
王磊 湯莉